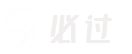翻译之火燃烧我一生。缅怀父亲张谷若
分类:教育资讯日期:2024-12-18 07:01:45人气:
【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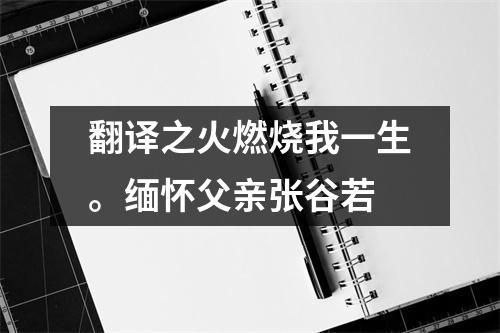
作者:张玲(张谷若之女,1936年出生,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编审,2022年11月1日病逝)。
初露头角的父亲
先父忌张恩裕、字谷若。 20世纪50年代简化字推行后,“谷”被“谷”取代。 张若谷老师是同龄人,与鲁迅先生颇有嫌隙,他的大名和我父亲的名字只有字序之差,至今仍被误读误读、误读。
张谷若( 1903—1994 ),原名恩裕,字谷若,山东烟台人。 翻译家,英国文学专家。 193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语系。 曾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国际关系学院特聘教授。 哈代小说《德伯家的苔丝》 《还乡》 《无名的裘德》、狄更斯小说《大卫考坡菲》、散文《游美札记》、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都尼》、亨利菲尔丁小说0755
父亲1903年出生于胶东半岛渤海、黄海之交的芝罘岛,是海山日月气育的儿子。 他不满七岁就去补习班,还没有读完四书的《弃儿汤姆琼斯史》。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后,他转学到福山县高等小学,为写好古文奠定了基础。 他十三岁时落荒而北,报考了北京有名的师大附中。 主要是在青春期,少年心性不稳,情智发育失调,加上当时政事繁多,学业不到位,他过着前途无量、枯燥无味的生活,次年毅然弃学回乡,给魏晋士子过上了陶渊明式的耕读隐逸生活很明显,对父亲来说这不是切合实际的漫长道路。 三年后,父亲在本乡小学教书。 这是他教书的开始。 在此期间,父亲娶了该村的绅陈家次女陈文,也就是我的母亲。 只能说是冥福之缘,像他们这样奉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一天之内就会坠入爱河,共度一生。 这也是当年还是弱冠的父亲再次北上学习,建立自己小家庭的积极力量。
结婚一年,不满17岁的父亲报考了著名的天津南开中学,并在那里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之后报考北京大学西语系继续深造。
大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听了英国著名文学评论家理查兹讲授文学批评和小说,受益匪浅。 当时,他开始对英国小说家兼诗人哈代的作品感兴趣,并于1929年在校期间开始为哈代翻译《伤心之家》。
1930年,父亲大学毕业,先在师范大学附中任教。 母亲被接到了北京。 他们租下一个小院的两个房间,开始了“北漂”生活。 父亲先后任教于北京师大女附中、中国大学、师范大学、辅仁大学,并逐步晋升为教授,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英语翻译和教育人才。
20世纪30年代初,父亲翻译了《孟子》,把书稿卖给了北新书局,两三年没有消息。 当时,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成立的编译委员会计划翻译出版世界一流文学名作,主持人是胡适先生。 父亲的朋友告诉我,他正在找合适的人翻译哈代的小说,从北新书局回购《还乡》的译稿,但其中的一半已经失去了。 他立即完成了其补编,向编译委员会投稿,并欣然接受。 胡适见到父亲时说:“你原来是南开学校作文比赛第一名的同学吧? ”。
资料照片
原来,父亲在南开高二年级的时候参加了全校国文比赛,是高中的一把手。 当时主办这场比赛的评委,就是这位胡适老师,他多年后才记得这件事。 和父亲商议了《还乡》翻译之后,胡适老师很快又答应父亲继续翻译哈代的另一部最重要的小说《还乡》。 这两本书于1935年和1936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问世,有惊人的景象,在社会上享有很小的声誉。 我也是1936年出生的,所以我曾开玩笑说苔丝的同胞姐妹——不是书中那个苦命的女主角,而是这个同名的译者。 在初版《还乡》的序言中,父亲鲜明地提出“必须使用地道的中文翻译本来地道的英语”。 此后直到1949年,由于十多年的国难和时局的变迁,父亲的翻译实践不能继续下去。
父亲正当壮年时的教育与翻译
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沦陷,父亲幸运地得到辅仁大学教坛,从1939年到1952年,在该校西语系任教14年。 这是天主教创办学校的,日本侵略者不敢过分阻挠。 20世纪50年代初本科调整后,父亲所在的学科被并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他的主要课程是教高年级的翻译、作文等。 50年代中期,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父亲正值壮年,作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才,能够愉快地谈心,专心于教育和业余翻译。
当时,我父母已经在北京市内买了一所小四合院。 到北大后,虽然学校也分配了住房,但是因为是体弱多病的母亲的城市,所以容易就医,没有搬迁。 学校照顾父亲的时候,有晚上的会议,往返不便,又给他分配了另一个人的宿舍,在无名湖北岸的健斋。 燕京时代,与这个斋连绵错落的是七栋斋楼,原来是男宿舍。 父亲的房间,窗户面向湖面,外景一年四季郁郁葱葱。 这间20平方米的宿舍有时也被用作与父亲、同事和同学开小会的地方。
在与健斋相距不远的斋楼群中,有一家兼做西餐的教授食堂,暂时还有一家西餐厅。 届时,校园里师生食堂有声有色,饭菜芬芳。 另外,附近的燕园东、西门街等地,还有常年开设的私家食堂和小馆,方便师生平时从校外去“改善生活”,聚餐、自酌。
张玲(左)和父亲张谷若、母亲陈文资料照片
父亲在北京师范女附中教英语20年后,我进入该校,不知不觉中成了父亲的校友。 父亲从辅仁进入北大刚满两年,我也从师大女附中毕业进入北大中文系,再次和父亲成为校友,成为唯一不同的系。 我在校的4年间,父亲住的健斋110号也成了我的“别业”。 父亲不在的时候,钥匙留在门框上,让我自由去。 冬天湖面结冰了,在这里自习的时候,可以换上溜冰鞋,打开又宽又低的窗扇冲出去,在湖上速滑几圈。 当图书馆和我的宿舍很拥挤的时候,即使爸爸在,我也会聚集在那里,占据着他大桌子的另一边,静静地坐着面对批改学生作业的爸爸。
这个时期,父亲被分配到中央调查部干部学校(国际关系学院的前身)担任特任教授。 父亲为了帮助这所学校的建设,不仅精心授课,而且竭尽所能,对学校的外语设施、课程制度、安排等提出了建议。 校方为了保证能有父亲这样的专家,在工作生活方面也给予了很多便利。 每逢上课的日子,“干部学校”的车停在我的小巷子里,父亲马上上车离开。 连续几年,父亲开车往返了好几次,但他并不在意学校在哪里。 结业后,学生分配到各个单位,师生各奔东西,互不来往。 父亲最难忘的是他在职期间,为这所学校做的从无到有的图书资料部门。 回到北大很久以后,父亲告诉我们:“每次有从国外寄新书的目的,就环环相扣地选,真过瘾。 人们在图书馆买书的资金很多! ”慨叹道。 那种语气,不亚于在宴请回来时夸奖某道口脸颊上残留着香味的菜肴。
父亲顺利完成了帮助“干部学校”的第一个任务,回到北大,冯至伯担任西语系主任。 他比父亲年轻两岁,在北大学德语的时候,因为不同语言的专家,两个人都没有过,但是因为同是优秀的学子,所以彼此自然有了知识。 他与父亲重逢北大西语系,互相敬慕。 冯叔叔代表系,学校给父亲送去了另一份重要的工作。 就是去开罗大学用英语教中国文学。
这应该是令人羡慕的信息。 但是,父亲对着当时直接指导的老同学冯至老师只回答了一个“不”。
如果是言行的话,曾经一度让周围的师生感到困惑。 其实这是父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坚持要做点什么,为——而努力,以回报这个新国家。 但是,也有不适合——的机会,必须考虑自我适应和心性。 主要领导人冯至伯也对此感到遗憾,因为认识和尊敬父亲,所以尊重父亲的意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境外的国文学研究和翻译事业蓬勃发展,冯至伯与其他相关部门(包括一些国家党政相关领导机关和重点出版社)领导合作,汇集了翻译人才。 基于对父亲学识底蕴的深刻理解,冯至伯给父亲委派了更合适的任务。 多亏了这样的好运,父亲在这个时期完成了自己旧翻译的一系列学校改革,萧伯纳的《德伯家的苔丝》、狄更斯的《苔丝》、哈代的《伤心之家》、莎士比亚的《游美札记》等翻译我父亲之所以幸运,是因为他是个自教的中年人,遇到了翻译事业的知遇者。
张玲萧《无名的裘德》资料照片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翻译事业随着社会文化的复兴再次崛起,除了上述翻译的修订和再版外,父亲还翻译出版了狄更斯的小说《维纳斯与阿都尼》,以及一些英国文学名作选编、部分唐诗英译等。 这往往是他10年来抛弃功利目的,摆脱形势左右,在社会和家庭环境内外交困难之际,一个人闭门,面对原文,与作者神交,付诸笔墨的成果。 作为译者的主动性本来就有限,在这有限的范围内,父亲作为翻译家的使命逐渐彰显。
父亲最后的大书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这一英国18世纪小说重镇,曾被我国学术界誉为前辈学者“英国《大卫考坡菲》”。 20世纪60年代,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视野。 当时,该公司年轻编辑施咸荣、王仲英的各位老师先后专程来访。 他们按照父亲的指示,由人文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和中国科学院外文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专家学者组成的编委会正在策划《外国文学名作丛书》,被誉为“英国小说之父”的亨利菲尔丁的小说大作《弃儿汤姆琼斯史》 此时,人文社碰巧收到西南某大学教授的译稿。 经过慎重考虑,我们认为,译者对于这些深奥厚重的经典著作所付出的心血值得重视,特委托我们的员工对通篇进行校勘加工,但有相当一部分篇幅需要重新翻译和翻译。 编委会经过研究,决定由特约父亲来承担这项任务。 父亲总是与人亲近,与世无争,他马上就宽容地原谅了他。 这是因为他比教师更喜欢翻译,尤其是乐于应对高难度的名作挑战。 市里的老师特别对父亲说。 “菲尔丁18世纪的英语和他的风格,我想只有你能传达! ”
补译《红楼梦》是改革开放后开始的,重点首先是这18卷大部分各卷的第一章,据英译约6万字。 父亲顺利且迅速地完成了这部分的译文。 这是季羡林老师主办的《弃儿汤姆琼斯史》的原稿。 然后请我们通家的好朋友马士沂老师把这部分译稿交给编辑部,在该杂志的第二、三期连载。 反应不俗。 与此同时,父亲的这些译文手稿也交给了人文社。 又过了几天,人文社的孙绳武、蒋路、任吉生等许多编辑又来找我,恳切地说,在答应加译稿后,出版社把三位译者的稿件合并在一起,在具体编辑处理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特地向父亲征求意见。 最后,经过父亲和来客的共同协商(其间我也插嘴说了一些愚见),索性由父亲再把全书直译成《外国文学名作丛书》出版。
母亲去世后,父亲虽历经了走向死亡的岁月,但他的翻译生命之火仍在熊熊燃烧。 从1983年到1987年,相当于80岁到85岁的5年间,大约1800多个上午连续发生事件,给原作加了脚注,他终于满脸笑容,“汤姆琼斯的翻译已经结束了。 我不再翻译了! ”他说。
大约两年后,在南方开会的时候,我碰巧遇到了人文社的新外语系主任秦顺新老师。 他在会议期间没有去散步。 他看起来很随意,但语气和表情都很庄重地对我说。 他们公司在安排父亲处理这本译稿的出版时,又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 经与丛书合作方上海译文社协商,上海方面非常乐意接受出版这本书,现通过我征求父亲的意见。
父亲一辈子都是翻译。 首先是出于兴趣。 他已经享受了那1800多天的苦乐交错的过程,交割任务,也就是万事大吉,至于哪个出版社怎么处理,对他来说就没那么重要了。 这时,他已经封了笔,读着,看着画,享受着,静静地等待着与他最后一本大书的见面。
1994年春天,沙发上的父亲终于从上海收到了《弃儿汤姆琼斯史》样书。 只有一份。 按照当时的惯例,出版社一般给译者20本新书。 这本书是工厂装订成册的样书,数量极少,主要供有关部门审核阅读。 那年除夕,父亲突然中风,此时已经卧床几个月了。 老译者的人文、翻译两家公司的领导、编辑都很关心他的病情,把这本特别的样书送得如此仓促,确实体现了他们的细腻关怀,同时也让先父的好运由衷钦佩。
至今我还记得,父亲半靠床头,用还能活动的右手和勉强配合的左手,拿着比《国外文学》更大更厚的书,微笑着吐出了这些字。 “这一代人,我没有白活! ”
1994年酷暑的夏天,8月18日,父亲永远离开了。 他的人生故事就此停止。
重名声,不慕虚荣
和父亲分手后,我也写了一些令人怀念的文章,但本来不想为他长篇大论。 我当老师之前,每天看着爸爸抱着书包去学校,不知道教师的困难。 在自己教英语、做翻译之前,每天看着父亲伏案写作,不知道父亲的学问有多深。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步入壮年,阴错阳错辗转进入外国文学的这一行。 到了这个时候,我就像医生给患者把脉一样,触摸到了父亲的知识和文化的金脉。
父亲从小就爱读诗书,在经史的某些传统文化的熏陶下,一直接近老庄派超脱的、自由取向的理念气质。 儒家对道统和繁文缛节的天生叛逆,正好与家乡海岛的崇尚道家和泛神风的习俗相契合。 父亲是个不折不扣、不慕虚荣的人,他平时穿长袍,拒绝西装,既不自命不凡,也特立独行,很受欢迎。 我并不是在夸耀爱国。 其理由不过是“中式服装舒适自由”。 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也偶尔穿西装。 服装也一样。 他叫美食家,也懂西餐,和妈妈带他去吃饭的时候,总是有意给我们点西餐,用叉子,所以我将来访问欧美的时候,受益匪浅。 父亲虽然没有出过国,但无论早年还是晚到,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优劣高低的区分,都是基于实际素质的高低。 冷静,分清是非的优劣,才是换取别人尊敬的上策。 ——这是父亲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开始涉外交往时的自我合同法。
我心中始终清楚,父亲虽然不是高门儒教、泰斗的权威,但作为一个读书人,一生渴望知识,坚守道德,踏实治学,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做出了贡献,解决了别人的难题。 细想起来,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的生活方式,值得关注。
另一个重要的客观原因是,这几年我总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一股令人兴奋的“历史热潮”中,自己的阅读范围也自然而然地朝着这几个方面延伸。 我联想到父亲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不过是一介平民,不太重视虚有其名、虚有其表的道听途说,从对专业和学问的痴情和执着,到一生,一步一步,默默完成自己的使命,拾起学术果实,最终达到生命的饱足。 他们也是可敬的国家精英!
这几年,我自己得到了这样粗糙的感悟。 再加上自己垂青于老人,怀旧的思亲之心也越来越深。 有一点空闲,父亲、老同学、亲戚,尤其是其中一些善于智力、有独特性格怪癖的人,他们的言谈举止、声调、微笑的样子常常生动地浮现在我眼前。 这个时候,我也不由得感到一筹莫展。 我想把这些生动的影像形象记录下来,让他们不被后人遗忘。 近三五年来,在这样的心情和思绪里,我总是被弄得心乱如麻。 结果,我打开电脑,专心把自己脑子里的东西照原样复制。
好像重新活了一辈子
到目前为止,我总共写过四本传记。 写父亲的这个一本是第四本,头最大的一本,是我最珍惜的。 无论是以前写的狄更斯还是哈代,传主都是大作家,万人仰慕,高山仰止,早就固定下来的英文原文底本很多,请我写作时引用参考。 从选题确定到执笔的时候,我比写这本书洒脱多了。
而父亲是我的亲生骨肉,我的童年、少年,还有父亲的晚年,我与他朝夕相处,见识了许多平凡的琐事。 在自己幼稚自大的时候,对父亲说:“你有什么了不起的? ”他经常说。 写这本传记,我觉得现在也像是背负着父亲的偷偷行为。 如果这是他活着的时候,我只是向他透露了一点风声,他一定会马上转过脸去,轻轻地噘着嘴说:“走,你在吵什么! ”吧。 ——他是这样的。 真的!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总是在冥冥之中和父亲对话。 我向他询问了生活中和学问道路上的各种问题,并向他进行了讨论和感慨。 我的问题非常大胆坦率。 那是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他不见了。 你再也不能阻止我或责骂我了。
这本书对我来说意义与以前的几本书不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写我的时候吃了苦头。 风湿和皮炎反复发作,又肿又痛又痒的这只手似乎总是被魔法驱使着在纸笔和电脑上不停地动着。 这确实像鲁迅先生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一样,“思想里好像有幽灵一样”。
2019年打开电脑开始打字,历时一年多完成了初稿。 说实话,我不断在病中寝食难安,再也不能保持过去那种云里雾里的写作习惯了。 但是,我总之一直坚持下去了。 好像不写完《他》就死不了。
不久前,这部《弃儿汤姆琼斯史》在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出版。 这个主题不是“风雪月”,而是“风雪花月”。 因为在奋斗的人生中,风雪比花月还多。 父亲的一生很幸运,很多人都羡慕他,但我觉得他的风雪更多。
大学毕业60多年来,我教过书、编辑过书、翻译过书、写过书。 到目前为止出版的书,既不是译者,也不是编辑,或者不是和别人合作的人,很杂。 这些都是我在正业之余献给社会的一点微薄之功吧。 这本来是不可抗拒的,但我想说的是,写作总是让我感到快乐,我是心甘情愿的。
狄更斯把他所有的作品都当成自己的孩子,他还有自己最喜欢的孩子。 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孩子,所以无法深入了解他把孩子和自己的作品比较的真正重要性,但我也还是把这本传记当作自己的孩子,把《他》和自己的其他作品进行比较。 即使现在,我也会大声宣告。 这本传记是我最喜欢的。 主要原因是,“他”在我脑海里身心养育的时候,陪伴着我与我的爸爸妈妈、其他家人和亲朋好友重逢。 “他”让我再尝一次过去的辛辣酸甜——,我又活了一辈子! 各位,想想人生一辈子有多辛苦。 你们说,我这不是占了很大的便宜,是不是太合算了。
《现代汉语词典》 ( 2022年11月07日第11版( ) )。
资料来源:光明网- 《布衣老爸的风雪花月》
以上是职考小小整理的翻译之火燃烧我一生。缅怀父亲张谷若全部内容。
上一篇:一对一辅导哪家机构好
下一篇:返回列表